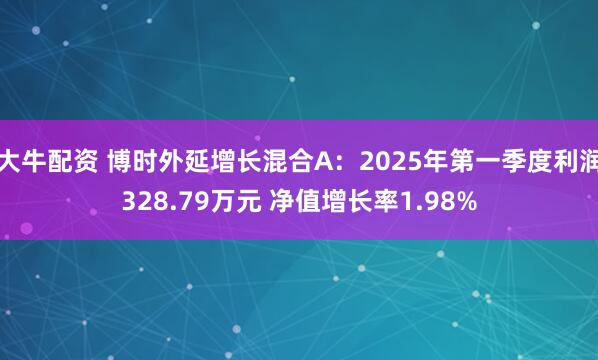云贵高原,作为中国四大高原之一,以其雄奇壮丽的自然风光闻名于世。其地理范围西抵横断山脉,东达雪峰山,南至红水河,北临长江,涵盖云南、贵州两省全域,以及湖南、广西、重庆、四川、湖北的部分区域。本文聚焦云南、贵州核心地带,梳理这片土地如何从汉朝的 “拓荒” 起步,历经无数反复天弘配资,直至清朝雍正年间 “改土归流”,最终彻底融入中国版图的漫长历程。
一、汉拓西南:“西南夷” 与中原王朝的首次深度联结汉朝时期,云贵高原上分布着众多部落与小国,中原人统称其为 “西南夷”。这些政权多深居群山之中,与中原交流稀少,在汉武帝之前鲜为中原所知。其中,夜郎国疆域最广,司马迁在《史记・西南夷列传》中记载:“西南夷君长以什数,夜郎最大”“夜郎所有精兵,可得十余万”,足见其势力之强;西部的滇国同样重要,传说是战国时期楚国将军庄蹻率军西征后建立的政权。由于长期隔绝,当中原使者抵达时,滇王与夜郎王竟先后问出 “汉孰与我大”,留下 “夜郎自大” 的典故,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西南与中原的隔阂。
展开剩余87%西南夷各国分布
汉武帝时期,为联合西南力量征讨南越国,派遣唐蒙出使夜郎。夜郎、且兰等国表示愿意臣服,汉朝随即在夜郎北部设立犍为郡—— 这是中原王朝在西南夷地区设立的首个行政机构,标志着云贵地区与中央政权正式建立行政联系。公元前 112 年,汉武帝出兵南越时,且兰国趁机叛乱,被汉军迅速平定。此后,汉朝以且兰为中心设立牂牁郡,对夜郎地区实行 “羁縻统治”(以当地首领为官吏,承认其部分自主权);又攻灭邛都国,设越嶲郡;随后进军滇国周边,消灭劳浸、靡莫两国,滇国见势归降,汉朝在此设立益州郡。牂牁、益州二郡的设置,意味着云贵大部分地区首次被纳入中原王朝的版图。不过,此时滇国、夜郎国并未完全消失,呈现 “郡县与王国并存” 的局面:汉成帝时期,夜郎王兴叛乱,被牂牁太守陈立诛杀,夜郎国灭亡;滇国则在归降后逐渐淡出史料,推测已名存实亡。
出土的滇国文物
西汉之后,中原王朝对西南夷的控制时强时弱,局势反复。两汉之交,中原战乱频发,西南各国纷纷反叛;东汉初年,才重新归附。公元 69 年,滇西的哀牢国归汉,汉朝设永昌郡,将统治范围延伸至滇西,但哀牢国此后仍多次叛乱。三国时期,西南夷地区被称为 “南中”。蜀汉在成都建立政权后,南中各郡拒不服从,永昌郡太守甚至投靠东吴,联合益州大姓孟获反蜀。诸葛亮率军 “七擒孟获”,多次镇压叛乱后才将南中纳入管辖,并将原南中四郡拆分为七郡,通过拆分势力来削弱地方割据基础。
蜀汉之后的两晋南北朝,因中原政权更迭频繁、国力衰退,对南中地区已 “鞭长莫及”。此前南中郡县由中央派遣的 “流官” 治理,西晋后逐渐被当地大姓取代 —— 这些 “南中大姓”(如爨、孟、李、董等家族)实际成为地方割据势力,虽名义上接受中原册封,实则自行其是。这种 “以夷治夷” 的间接管理模式,成为后来隋唐、宋元时期 “羁縻制度” 与 “土司制度” 的雏形。
二、唐宋羁縻:土司制度的萌芽与云贵局势的分化隋朝统一全国后天弘配资,国力有所恢复,重新将目光投向西南。隋文帝曾两次出兵击败南中爨氏势力,却未能彻底取代其地位;同时派遣田宗显任黔中刺史,试图控制乌江流域,为后续治理打下基础。
唐朝建立后,继续推进西南开拓,在云贵地区设立大量 “羁縻都督府”,如南宁州都督府(管辖云南东部)、黔州都督府(管辖贵州一带),分别隶属于剑南道与江南道。这些都督府的长官多由当地民族首领或大姓担任(如南宁州由爨氏掌权,黔州由田氏掌控),唐朝通过 “册封 + 纳贡” 的方式维系管辖,形成 “以夷制夷” 的羁縻体系 —— 这一制度虽能暂时安定边疆,却统治薄弱,也为后来土司制度的形成奠定了框架。唐玄宗时期,云南西部的南诏国崛起,南宁州都督府因无力抗衡被迫撤销,唐朝对云南东部的控制大幅减弱。
唐朝在黔中设置的羁縻州分布
738 年,南诏国统一云南六诏(乌蛮、白蛮部落联盟),成为西南地区的强大政权。唐朝曾多次出兵征讨南诏,均以失败告终。南诏国王虽名义上接受唐朝 “云南王” 的册封,实则为独立王国,甚至在唐朝后期多次入侵黔中、西川地区。因此,自唐朝中期起,云南大部分地区已脱离中央直接控制。南诏灭亡后,大长和、大理国先后继承其统治,其中大理国在宋朝时期与中原保持 “藩属关系”,双方和平相处,大理国成为宋朝西南边境的 “缓冲政权”。
大理三塔
与云南的失控不同,黔中地区(今贵州一带)成为唐朝中后期的经营重点。开元年间,唐玄宗将江南道拆分为江南东道、江南西道与黔中道—— 尽管当时黔中人口稀少、经济落后,尚不具备单独设 “道” 的条件,但因其地处云贵高原东部,是遏制南诏东扩的战略屏障,故被单独列为一级行政区。唐朝末年至北宋时期,中央王朝在黔中扶持地方大姓,逐渐形成四大羁縻政权:播州杨氏(占据今遵义)、思州田氏(占据今铜仁、黔东南)、水东宋氏(占据今贵阳)、水西罗氏(占据今毕节)。
海龙屯:播州杨氏建立的军事遗址
两宋时期,四大姓成为中央王朝在西南的 “代理人”:北宋时,思州田氏势力最强,曾担任 “贵州防御使”,协助朝廷平叛;南宋时,播州杨氏崛起,不仅多次拓展地盘,还曾六次击败蒙古大军,并协助南宋将领余玠修建钓鱼城(抵御蒙古的重要防线),成为西南抗蒙的重要力量。
三、元明清:从行省设立到 “改土归流”,云贵彻底融入华夏1252 年,忽必烈率领蒙古大军南下,灭亡大理国,意图从西南迂回包围南宋。大理灭亡后,忽必烈采取 “怀柔政策”,任命大理段氏为 “大理国总管”,同时派兀良合台率军驻守,段氏政权实则沦为傀儡。1271 年元朝建立后,推行 “行省制度”,在大理设立云南行省,这是云南首次成为省级行政区。元朝在云南大规模设置州县,尝试推进 “改土归流”(将土司管辖改为中央派遣流官治理),但此举激化了与段氏的矛盾,元朝末年,驻云南的 “梁王”(元朝宗室)与段氏政权冲突不断,云南局势再度动荡。
云南行省
1381 年,明太祖朱元璋派遣傅友德、蓝玉、沐英率领 30 万大军南征云南,次年击败云南梁王与大理段氏残余势力。明朝在云南设立 “云南布政使司”(行政)、“云南都指挥使司”(军事)、“提刑按察使司”(司法),完全仿照内地省级建制。在此基础上,明朝进一步推进 “改土归流”,并实施 “移民实滇” 政策 —— 大量中原百姓迁入云南,开垦土地、传播技术,使云南大部分地区的经济、文化逐渐与内地接轨。
滇池
此外,元朝曾将势力延伸至缅甸、老挝、泰国北部,设立土司机构;明朝继承这一管辖,将这些区域整合为 “三宣六慰”(三个宣抚司、六个宣慰司),名义上归云南都司管辖。但明朝对 “三宣六慰” 的控制仅停留在名义层面,未派遣军队驻守,因此即便在谭其骧主编的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中,也未将其划入明朝疆域。明朝后期,缅甸、泰国等国统一后,“三宣六慰” 的名义管辖也随之撤销。
三宣六慰地区
在贵州方面,元朝统一后,黔中四大姓纷纷臣服,元朝将其册封为宜抚司、宣慰司,形成贵州历史上的 “四大土司”。明朝建立后,四大土司继续归附,明朝在水西罗氏(后被赐姓 “安”)、水东宋氏领地设 “贵州宣慰司”,以其首领为长官;同时分别设立播州宣慰司、思南宣慰司、思州宣慰司(思州田氏后分裂为二)。为加强控制,明朝在土司辖区的重要驿道驻军,并设立 “贵州都司”(省级军事机构),监控四大土司动向。
明代贵州地图
永乐年间,思州田氏爆发内乱,永乐帝趁机出兵平定,将思州、思南土司故地拆分为 8 府。1413 年,永乐帝将贵州宣慰司与这 8 府合并,设立贵州布政使司—— 这是贵州建省的开端,也是贵州 “改土归流” 的关键一步。此后,贵州省疆域不断扩大,都匀府、程番府、普定府等先后被纳入管辖。1600 年,播州杨氏叛乱,明朝平定后将其拆分为遵义府、平越府,分别划归四川、贵州;1630 年,水东土司叛乱被平,设开州(今贵阳开阳),隶属于贵阳府,贵州宣慰司也改称 “水西宣慰司”。
甲秀楼
清朝初期,水西土司叛乱,清廷平定后设大定府(今毕节大方)。1727 年,雍正帝将原属四川的遵义府划入贵州,至此贵州版图基本定型。雍正年间,清廷在贵州大规模推进 “改土归流”,尤其在苗族聚居的 “苗疆” 地区,设立古州、清江、台拱、丹江、八寨、都江六厅(史称 “新疆六厅”),彻底废除土司特权,由中央派遣流官直接治理。至此天弘配资,贵州自明朝开启的 “改土归流” 全面完成,正式成为 “汉地十八省” 之一。中原文化(如儒家思想、科举制度)在贵州广泛传播,催生了 “沙滩文化”“花溪文化” 等具有较高水平的汉文化流派,推动贵州经济、文化实现跨越式发展。从汉武帝设立犍为郡的初步探索,到唐宋羁縻制度的间接管理,再到元明清行省设立与 “改土归流” 的深化,云贵地区融入中国版图的过程历经 1800 余年。这段历史不仅是中央政权对边疆治理不断完善的历程,更是云贵各族与中原民族在文化、经济、血缘上深度融合的见证,最终奠定了今日云贵作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历史根基。
发布于:浙江省永华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